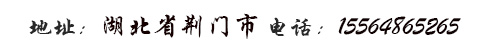白玉稳家真的在梦里了
|
约 美文 家真的在梦里了 作者:白玉稳 又一次进山去了! 按理说是回家,但客观上家没了,再说回家,就有些词不达意。 家是有血亲居住的地方。 能进家门,看不到家人,这种感觉是欲哭无泪。 男人的眼泪在肚子里。就像山里的地下潜泉,轻易不会冒出来。 汤峪这条路,走了半辈子。不对,人一般活不到一百岁,应该是大半辈子了。 过去回家,脚腿有劲,几十里山路,就是步行,也两三个小时足矣。有条件开车了,回家更快。 心里有念想,干啥都是有劲儿的。回家,就是家里有念想有牵挂。 父亲的烟袋,母亲的锅灶,哥哥的石头,嫂嫂的药箱,还有侄儿侄女的学习生活用具,在我眼里都是有温度的散文和诗,不再是冷硬的物件。 哥哥是爱石头的。开始我不理解,山里人,整天和石头打交道,烦都烦死了,你干的活重人很辛苦,怎么还在劳作间隙,去寻找石头,往自己的院子里搬。为这事,嫂子没少嘟囔他,可是他初心不改。我家有多少奇形怪状的石头,真没统计过,凡是能看得到的地方,凡是能放的空隙,都放置着哥哥的石头。 哥哥平时口笨,不太会说话,但是如果有人来看他的石头,就如同欣赏他的一对儿女,他就会耳清目明口如悬河。会不厌其烦地给人说,这块石头是从哪里弄回来的,它像个啥,不信你仔细瞅瞅,再认真看看,不行再闭眼想象一下,它的形状,它的图案,像什么?直到人家说像,说真像!他就会挠头幸福地笑,一天的劳累都消失不见了。 院子有一块大石头,我不知道它是怎么被哥哥弄回来的,反正一个人是拿不动的。他开始放置在大门内,一回来就看,后来家里开农家乐,就放在了院子里,凡是来家和路过的人都能看到。有人说是一头羊,有人说是一头鹿,特别是那四个蹄子,那个身子,以及回头的神态,栩栩如生,人见人爱。他喜欢很正常,所有的人都喜欢,常常在石头前驻足观看。有城里的奇石收藏家看到了,想买走,且价格一路飙升,哥哥是坚决不卖。他说,他喜欢石头,那些石头是有生命的东西,就应该在阳光雨露中生长,如果进了温室,我怕它失去灵性。 昨天我回去,在院子里看到了这块石头,石头上的动物依然回头看着我,可是伺弄它的哥哥不在了。哥去了天上。不知道天上的云朵是否会变成哥哥喜欢的石头。 屋后的山坡,长满了杂树,不成才,但能遮阴,能玩耍。四季的林子里,都有童话和故事。 门前的大河,水依然在淌,不下雨,不发山洪,就没有大的声响,温柔地像情歌,唱给懂的人。 河上巨石上的木桥,早已不见踪迹,代之而起的是石拱桥,威武了,结实了,却少了诗意。 喜欢在河道里玩耍。可以用目光数小石潭里游弋的小鱼,可以用耳朵听山坡鸟的歌唱,可以在树林里捉迷藏,可以躺在石头上假寐胡想…… 山里的天是不规则的图案。老家上店的天空,永远是长方形的。小时候,坐在家门口的石头上,向上向下向左向右仰视,那个形状永远是固定的,能变动的就是云彩。早上的太阳从东边山上升起,不到傍晚就隐在了西山。夜晚,天晴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星星在框子里装着,很少动。 我以为所有的山就是这样。 我以为所有的天也是这样。 小时候的我和好多山里人一样,以为一辈子就是这样看下去,看着逼仄的天。没想过有一天能走出去,也没想过有出山的路。属于自己的路。 我是幸运的。还是走出去了,终于知道,原来天很大,是老家上店天的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几万倍大……原来山里是有路的,越往外走,路越宽大,最后通向远方,连接五湖四海。 因为走出来了,在外边有许多不适应,有许多委屈,就想到了回家。山里的男人不在外边流泪。就是想哭,也会回到山林里,回到家里,家人不会笑话自己。这时的家,就是人们口中的港湾。在我心里,它还是疗伤的地方。 家里疗伤不用药,就是父亲的烟酒,母亲的饭菜,还有儿女绕膝。人是矛盾的主体。不出去闯荡,没有生活的改善,在外边不和谐了,就得回家休养。 别人是有家的。我现在没了。虽然山还高耸,水还长流,房前屋后景色依然,可是没亲人的房子就不叫家。现在回去,自己都觉得别扭,常常在家门口不得进入,黯然神伤。 现在进山不叫回家。尽管乡亲依然在说,“回来了?”我也在答应,“回来了。”可是我知道,我是真的又一次进山了。我回到了山里,回不到我的家里。 出山后,昨晚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全是老家当初的样子,还有我健在的亲人们,特别突兀的是,梦里有太多奇形怪状的石头。醒来,我流泪了,我知道我的老家,只能在梦里了。 白玉稳:笔名子玉,陕西蓝田汤峪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工作之余,喜欢文学,涉猎诗歌、散文、随笔等,已出版散文集《白云深处》《百味》。 约 美声 主播:李慧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省作协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杨凌融媒体中心总编室主任。出版散文集《樱桃鹿》。作品散见于《延河》《陕西日报》《文化艺术报》《燕赵都市报》《宝鸡日报》等报刊杂志。 约 美评 汤峪白先生的 人生“百味”与乡土书写 作者:庞洁 白玉稳,人称“汤峪白先生”。既是教师,也是作家。 “师者,所谓传道受业解惑。”这说的是一个老师的职业使命,但当“老师”还原为普通的写作者,他首先要做的是自我觉醒。人品良善质朴的人很多,但在写作上,要做到“真”并不是很容易,我读白先生的很多文章,感觉就是听一位长者讲他的经历,讲他小时候走过的木板桥,他对山外生活的憧憬,他不掩饰自己曾经的贫瘠,他不掩饰自己的局限,他是敢于袒露自己并富有自我鞭挞精神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几乎说的就是白先生的写作,明世故,通人情,熟悉江湖,善于应对矛盾,而自己又完全不世故,古道热肠、了解社会,更了解自己。也正是基于这种了解,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语言风骨,这一点对作家来说是最难得的。 从写作题材上看,作家孔明老师把白老师的文章比作“村姑”——“七分长相,三分打扮,未必入时,却吸引眼球。”很多乡土散文其实都具备村姑的特点,可是白先生塑造的村姑让人觉得赏心悦目,就是因为她不矫饰,她没有刻意地给自己穿个城里时髦女郎的靴子,再喷一点香奈儿香水,甚至还要去美容院打玻尿酸、纹眉隆鼻,更有甚者,本来从小名字就叫“小翠”挺好的,非要给自己起个玛丽或安娜的洋名儿招摇村头,让村里的老人都惶惑不已。前段时间,作家梁鸿和石一枫在《文艺报》有一个“关于城市文学与乡土文学的对话”,题目非常贴切,叫《在生长中彼此塑造》,城乡绝不是“二元对立”的,是彼此在塑造的。梁鸿笔下的农村问题之所以引起了普遍的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ibue.com/bbcd/5633.html
- 上一篇文章: 看这里提高生物农药防效要做到ldqu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