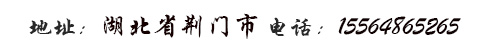七个一百百部凡人小事纪实进城
|
村西,有一条官道。 小时候,官道是一条土路,深深的车道沟仿佛两条铁轨伸向远方。官道笔直,向北直通高保公路,往南连着小镇。那时,官道离村子很远,但是放学后,我们都愿去官道边,打草或是玩耍,因为那里可以看汽车。 当时,官道上跑的多是胶皮轱辘的大马车,汽车绝对是稀罕物。只有一早一晚,可以看见汽车——绿色大卡车。车身上的绿漆早已斑驳不堪,但一路喇叭鸣叫,很是神气,惊得我们捂着耳朵四飞八炸。大卡车来自保定,是专门接送人们进城的公交车,一路上走走停停,不断有人上上下下。年轻人上下车直接攀爬,上边拽下边托;上岁数的则要从车后竖下一个小梯子。 公交车早晚各一趟,错过就只能等第二天。那时,常见背着大包小包、着急忙慌往官道跑着赶车的身影。车是敞篷的,人站在上面晃来晃去,像是被风刮得东倒西歪小树。遇到刮风下雨更惨,人好像从土里、水里爬出来的,泥猪疥狗一般。即便这样,也不是谁都可以轻易坐车进城的,尤其是我们小孩子,啼哭也没用,就是不带着去,一张车票好几毛钱呢。“不带拉倒,谁稀罕?跟拉猪的似的。”我们故意说着气话。爷爷一瞪眼:“可不兴这么说,人得知足,现在强多了,早先进城都得走着,一天打来回,两脚的血泡,钻心的疼。” 上师范二年级时,官道修成柏油马路,公交车也换成了大客车。那时已分田到户,闲暇时,乡亲们进城的日渐多起来。公交车增开到每天四、五趟,还是爆满,车厢里挤得登登的,连个插脚的地方都没有。一次返校,天气闷热,车上人又多,不一会儿,便有点晕,又动弹不得,强忍着上了高保路,刚想推开身边的人,张嘴说“让开点”,不想“哇”的一声吐了出来,喷得一位大叔浑身都是。 市里的公交车窗明几净,干净豁亮多了,发车也准时,一会儿一趟。售票员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燕语莺声的,很是好听,心想:将来就找个这样的媳妇。最令我佩服的是,那时没有投币箱,一站不管上来多少人,也不管你坐几站,售票员都能快速准确地撕票找钱,手脚麻利,记忆清楚,想蒙混过关的,绝逃不过人家的火眼金睛。老人、孕妇一上车,“唰唰”站起好几位让座,城里人素质就是高!咱乡下野小子也不甘落后,几次让座赢得赞许的目光,心里美滋滋的。 年暑假,调往县城上班,老婆孩子留在乡下。县城还没通公交车,只好骑辆破摩托来回跑,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那罪受的。好在年底,开通了5路公交车,省去了顶风冒雪之苦。车只开到镇上,早上须早早骑车赶去,把车寄存在车站附近,晚上再骑回家。早班车很不准时,几次晚点上班迟到,只好走后门溜进办公室。年农历7月16日,举家迁到县城,不久堂兄打有2路车了,打咱们村穿过,听见喇叭声再出门都赶得上。后来知道,我们村的喜同买了辆车,专跑2路线,坐车提前电话预约,车到哪了实时沟通,一点都不用着急。 现在,县里开通了十几条公交线路,覆盖着大部分乡村,想去哪儿去哪儿,县城的几路公交也好几路,犄角旮旯都跑遍。去年,年近古稀的叔叔、婶子从石家庄搬回县城,整天不失闲,去公园、逛超市、跑菜市场,还常发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ibue.com/bbgx/9062.html
- 上一篇文章: 篇19年级部编版语文必背古诗词,
- 下一篇文章: 加入年度漫画会员,百部最新漫画免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