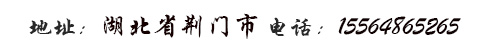通鉴易知录第6集国运之辩
|
天下大势,无非纵横。随着第一次合纵联盟破产后,六国纷纷选择与秦国求和,选择“事一强以攻众弱”的连横策略。此时,秦国和赵国,在面对国家发展战略的抉择时刻,两国精英各自在朝堂上进行了一场国运之辩。秦国对东出和南向的两条道路进行辩论,而赵国对北上和南下的两条道路进行辩论。今天,我们继续学习《资治通鉴》,复盘这两次决定国家命运的朝堂之辩。 一、朝堂之辩(秦国) 公元前年,巴、蜀两国互相攻击,双方都向秦国请求紧急支援。秦惠王本打算征讨蜀国,又觉得道路艰险狭隘,*队不容易到达,且韩国还有可能趁机侵扰,故而犹豫之中难于决断。司马错建议出兵攻打蜀国,张仪则说:“不如攻打韩国。”秦惠王道:“请让我听听你们各自的理由。” 张仪道:“我们先与魏国亲近,与楚国友善,而后向韩国的三川地区出兵,攻占新城、宜阳,将兵锋推进至东西周的城郊。之后占据周王室的九鼎,掌握天下的图文资料,挟持周天子以号令天下,则天下没有敢不遵从的,这才是一统天下的王业。臣听说,争取名位就要在朝堂上争,争取利益就要在集市上争。如今的三川和周王室就是天下的朝堂和集市,大王不在此处争夺,反而跑到边远地区去与戎狄小国争夺,这就离王业太远了。” 司马错说:“不对。臣听闻,要想让国家富裕,就必须使领土扩张;要想让*队强大,就必须使百姓富裕,要想成就王业,就必须使德*广博。只要三方面条件具备,则王业是随之而来、水到渠成的事。现如今,大王您的国家土地狭小、百姓贫穷,因此臣请求您先从容易的事情开始做起。蜀国地处西部边陲,首领又是戎狄之君,像桀纣一样昏乱。以秦国之强去攻打蜀国,就好像是让豺狼去驱逐群羊。占据了蜀国的土地,就可以用来使秦国的疆域扩张;夺取了蜀国的财货,就可以使秦国的百姓富裕;整顿武装部队后,不需要造成太多杀伤,即可令对方臣服。攻占一个国家而不会让天下人觉得暴虐,获取无尽的利益而不会让天下人觉得贪婪,可以说是只要我们一采取行动,就能获得名副其实的利益,同时还能博取禁止暴乱的美名。如果现在攻打韩国,挟持周天子,则获得的是坏名声,而且也未必会有实际的利益。出征时背负着不义之名,攻击的对象又是天下人不愿意我们攻击的,这样做就太危险了。周王室,是天下各国的宗室。齐国,是韩国的盟邦。一旦周王室知道自己将失去九鼎之宝,一旦韩国知道自己将失去三川之地,则必将通力合作,借助齐、赵的力量而向楚、魏求援,倘若周王室将九鼎送给楚国,韩国将三川之地送给魏国,届时大王您也无法阻止,这就是臣所谓的危机所在。比不上伐蜀那般稳妥。” 秦惠王听从司马错的计策,发兵攻打蜀国,十月占领。自从蜀国归属之后,秦国变得更加富庶强大,也因此更加轻视各诸侯国。 二、胡服骑射(赵国) 公元前年,赵武灵王与肥义谋划用胡服骑射来教化百姓,道:“愚者所嘲笑的,正是贤者所洞察的。即便全天下的人都嘲笑我,我也要这样做,必须得把胡人和中山国的领土都兼并过来。”于是改穿胡服。 国内百姓都不愿意穿胡服,公子成称病不上朝。赵武灵王派使者前去请公子成道:“家事听命于尊长,国事服从于君王。现在我要求百姓改变服装而叔父您不肯穿,我担心天下人会议论我这是在徇私情。治理国家有一定之法,总以有利于人民为根本;处理*事有一定之规,总以能执行命令为优先。施恩德要先从下层开始,行*令则要先从上层开始,因此我希望能够仰仗叔父的高义,以完成改穿胡服的功业。” 公子成再拜而行礼道:“我听说,中国是圣人教化的地方,是礼乐普及的地方,是远人前来观察的地方,是外族学习仿效的地方。如今,大王舍弃这些而改穿远方外族的服装,变更自古以来的传统,违背全体国人的心愿,我恳请大王能够慎重考虑。”使者回报赵武灵王。 赵王于是亲自登门解释,道:“我国东面有齐、中山;北面有燕、东胡;西面有楼烦、秦、韩。现在没有骑射的武备,如何能够守住国防?先前中山依靠齐国的强兵,侵犯我们的领土,掠夺我们的人民,又引河水围鄗城,若非社稷神灵庇佑,鄗城几乎就要失守了。先王以此事为奇耻大辱,所以我才下决心要改变服装,训练骑射,目的就是要能够防御四境的兵患,血洗中山的仇怨。可是叔父您只是一味依循中国之旧俗,排斥变服之名声,却早已忘记鄗城事件的耻辱,这是让我感到失望啊!”公子成服从命令,于是赵武灵王亲自赐给他胡服,第二天便穿胡服上朝。于是,赵武灵王这才下达胡服令,而后教导人民练习骑射。 公元前年,赵武灵王派楼缓出使秦国,仇液出使韩国,王贲出使楚国,富丁出使魏国,赵爵出使齐国;命代相赵固主持胡人事务,招募胡人充实*队。 公元前年,赵武灵王灭亡中山国,中山国君逃奔齐国。 事实证明,双方都做了正确的选择,秦国通过南下吞并巴蜀,巩固后方后变得更加富庶强大;赵国通过实施胡服骑射改革,向北发展吞并了中山国,不仅没有卷入中原诸侯的混战,还趁乱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双方的正确决策,也促成了战国后期两强鼎立的局面,也为秦赵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做了铺垫。下面我们结合战国时期的地图(来自布哈林大神),来点评下两国的战略选择: 先说秦国的朝堂之辩,我们以公元前年秦国吞并巴蜀前的地图为例。 秦国所处的关中平原,北面是*土高原,西面是陇山,南面是秦岭,秦国要通向中原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取道渭河平原出函谷关进攻魏国,一条是通过汉中地区出武关进攻楚国。自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后,历代秦国君主都将东进中原争霸视为国策,但受到地缘的限制,秦国要想东出,就必须要和魏国和楚国进行战争。仅仅2年前,楚魏韩赵燕五国组成合纵联*兵临函谷关下,虽然秦国获胜了,但外交备受孤立的滋味并不好受。恰好此时,秦国西南方向上的蜀国、巴国、苴国之间发生了战争,都请求秦国出兵救援,秦国关于下一步的战略出击方向,出现了两种选择。一条是春秋以来争霸的老路,另一条是韬光养晦的新路。 对于秦惠王来说,这个战略选择远没有现在看来这么容易。古来雄主多好大喜功,张仪“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的策略,非常迎合秦惠王称霸的心理预期。站在当时的时代,张仪认为打下巴蜀没有实际利益,属于很正常的判断。因为当时的巴蜀并不是“天府之国”,反而因为蜀道难走,导致巴蜀的生产力非常落后,居民都是蛮夷,占领巴蜀不仅无法直接获益,还需要秦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扶贫开发。有点类似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年从沙俄手里花了万美元买下阿拉斯加,当时美国*客和记者认为阿拉斯加是一片贫瘠的荒地,购买阿拉斯加这件事被俗称为“西华德的蠢事”。因此,这一点上张仪的建议有其合理之处,不能从结果反推他就是错误的。 但司马错是一名优秀的战略家,他并不只是从*事上看问题,而是始终站在秦国兼并天下的角度来思考。他指出,秦国还没有真正“问鼎”天下的实力,如果进攻韩国威逼周王室,周天子会把九鼎送给楚国、韩国也会全面投向齐国,同时,因为秦国犯了众怒,六国又会结成新的合纵联盟,天下势必联合伐秦,秦国无疑将彻底孤立,面临着巨大的亡国压力。司马错坚持攻占巴蜀,是为秦国规划了百年大计。他敏锐地意识到,一旦六国失去了秦国的*事威胁,六国就会重新分裂相互讨伐,在六国陷入混战的时期,秦国吞并巴蜀可以为秦国创造了一个资源根据地和稳定的大后方。事实上,中原各国对于秦国的这次版图的大幅扩张并没有强烈反对,秦国成功地在不惊动六国的前提下扩充了秦国的势力。秦国吞并巴蜀后,通过任用李冰修筑了都江堰,让巴蜀成为天府之国,后期为秦国关中之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粮草支持。 我们再说赵国的朝堂之辩,我们以公元前年赵国的地图为例。 自三家分晋以来,赵国分得的土地,主要是在晋国的北部区域,位置比较偏远,土地比较贫瘠,生产力水平低下。周边邻国,西面有秦,南面有韩、魏,东面有齐,东北面有燕,西面和西北面则是楼烦、匈奴等游牧部落,此外还有白狄建立的中山国,从东面嵌入赵国的中部腹地,阻碍赵国的南北交通。赵国历代君主一直都是坚持南下经略中原,赵国看中的目标是位于赵、魏、齐三国之间的卫国,然卫国是魏国的附属国,遂导致了自前年开始的赵伐卫、魏伐赵、楚伐魏的中原混战。战后,魏、赵、卫均遭重创,反倒是二十五年前被魏国所灭的中山得以复国。此后近五十年的时间里,赵国一直试图攻占卫国和中山,但皆因魏、齐两大强国的干预而进展甚微,甚至屡遭重挫。 公元前年,赵武灵王即位,之后十余年间,赵国在与齐国和秦国的交战中连续遭到挫败,北面的胡人和东面的中山也屡屡乘机进犯,这促使赵武灵王重新思考赵国的战略发展方向。经过北上实地考察,赵武灵王决定改变赵国百年来的战略,将战略目标由向南经略中原,改为兼并东边的中山和北边的胡人,在外交上与其余六国皆保持友好,在列国称王的背景下,赵国坚持不称王,不参与合纵连横的任何一方,始终保持中立态度。由此,赵武灵王提出了“胡服骑射”,要求全民脱掉中原固有的宽袍大袖,改穿胡人的短装,束皮带,穿皮靴,以方便骑马射箭,训练出强大的骑兵*团,向北拓展赵国的生存空间。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出,赵国的疆域大体可以分为两块,以首都邯郸为中心南边领土,位于华北平原,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经过数代君主的经营,这里成了赵国的精华之地。西北部以晋阳为中心的这块领土,是赵国祖宗的龙兴之地,也是当年赵襄子击败智伯的地方。这块领土与楼烦、林胡等少数民族接壤,地形以山地和草原为主,称为“代地”,人民半耕半牧,民风剽悍。地理上的天然隔绝,将赵国分成了“邯郸派”和“代地派”两股针锋相对的*治势力。在赵国百年南向发展的战略下,赵国朝野一直以“邯郸派”占大多数,以公子成为代表的赵氏贵族是邯郸派的领袖,他们天然反对改革,自然反对胡服骑射。真实历史上,赵武灵王不仅是靠登门拜访,还是用了很多*治手腕才勉强让“邯郸派”接受改革。其实,赵武灵王搞胡服骑射并不只是简单的*事改革,主要目的是捏合“邯郸派”和“代地派”两股势力,统一内部思想,实现君主集权的目标。由于战国史料的缺失,我们对胡服骑射的具体举措了解较少,但可以指出的是,胡服骑射绝不是后人认为换件衣服、训练骑兵的简单改革,必然是涉及到*事、*治、经济、文化改革的全面改革,正因为改革阻力极大,故而其它国家根本无从效仿,使得赵国成为日后东方六国中唯一能在*事上与秦抗衡的强国。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成功后,就把目光锁定在中山国上。为此,赵武灵王派出外交使节进行斡旋,楼缓出使秦国,仇液出使韩国,王贲出使楚国,富丁出使魏国,赵爵出使齐国,为赵国营造有利的外交环境。公元前年,当秦、楚、齐、韩、魏五国在宛郡混战之际,赵武灵王趁机出兵讨伐中山,其余五国既无心、也无力出兵干预,遂导致中山为赵所灭。 下图是公元前年的战国地图,可以明显看出,经略巴蜀后的秦国,实现胡服骑射的赵国都实现了领土的快速扩张,国力得到大幅增强。 下面按照惯例,我提出一些问题供读者去深度思考。 一、如果你是秦惠王,面对双方各执己见的情况,你应该如何做决策?如果接受了司马错的意见,你该如何安抚张仪?如果接受了张仪的意见,你该如何安抚司马错?如何避免朝堂上的争论演变成不同路线的*争? 二、请思考为什么秦国总能吸引来自六国的顶级人才,实现朝堂上人才济济?而六国要么像商鞅这样的人才出现流失,要么像屈原这样的爱国之士遭到冷藏,秦国历代国君在识人用人上有什么秘诀? 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让赵国成为与秦国争雄的强国,但相比商鞅变法,赵国的后劲不足,最终被秦国兼并。如果你是赵武灵王,当赵国向北发展已经到达极限后,势必要向南重返中原,赵国应该如何谋划发展自己? 四、二战时期,纳粹德国也面临着同样的战略抉择,是向西跨越英吉利海峡攻占英国,还是向东攻击苏联。最终纳粹德国选择了进攻苏联,陷入双线作战导致灭亡,如果纳粹德国选择向西灭了英国,那么历史又会如何演变呢? 毫无疑问,秦惠王是一个知人善任的好领导,秦惠王虽杀商鞅而不废商鞅之*,虽宠张仪而不尽听张仪之言。可见,秦惠王的用人水平之高,既允许下属有不同意见,又能团结下属一心共创大业,实乃我辈应该学习效仿。姚尧在精读资治通鉴一书中关于领导者用人之道有段精彩的评论,特此摘抄如下: 正确处理部属提出的不同意见,是衡量领导者素质的最重要指标。譬如说,部属甲和部属乙发生争执,平庸的领导者此时通常会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是听听甲说的有道理,听听乙说的也有道理,遂致内心犹疑而难以决策,甚至放任甲乙恶斗以争出胜负。袁绍之败于曹操,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第二种是明确表态支持甲,同时强迫乙也必须全力支持甲,否则就对其严厉处罚。北宋因新旧*争而亡国,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真正高明的领导者,一方面会明确表态支持甲,但另一方面对乙给予足够的尊重和礼遇。盖只要甲乙二人没有叛变投敌,则其观点都必定是有一定道理,也存在一定问题的。领导者支持甲的观点,并不表示甲的方案在执行中不会碰到任何问题。领导者没有支持乙的观点,亦不表示乙的思考完全没有道理。通常,乙所忧虑的,正是甲容易忽视的。甲所欠缺的,亦是乙能够补强的。只有给予乙足够的重视和礼遇,令其时时提醒劝谏,才能保证甲的方案在执行中不因细节纰漏半途而废,亦能保证乙不会因心怀不满而对甲暗地使绊子。更重要的,也许当甲的方案执行一段时间后,发现当前无法顺利推进,不得已还得重新回到乙的方案上来,如果最初把事情做得太绝,则牵涉到的人事倾轧会非常严重。故高明的领导者,支持甲时,能让乙同心协力;之后即便转而支持乙,亦能让甲毫无怨言。而最昏庸的领导者,是根本不听进部属的建议,凡事只凭着自己的情绪恣意妄为,要是有人胆敢违逆其心意,则必定加以严惩,甚至杀戮。所导致的结果,必定是在疯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却没有人再敢说话。 其实,大部分领导者都懂得权力制衡的道理,但这又很考验管理者的能力水平。现实生活里,大部分领导者都是姚尧所说的第一种和第二种情况,能做到第三种的领导者少之又少。在朝堂争论后,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吞并了巴蜀,没有让张仪伤心,更没有让他心生不满。反而会让张仪更加敬佩秦王的贤明和聪慧。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是一种“千里马”遇到“伯乐”的欢喜,也是“良禽择木而栖”的智慧,反而更加珍惜与秦惠王的君臣之情。秦惠王一方面让司马错镇守巴蜀以抚平人心,另一方面也授权张仪出使楚国,才有了著名的张仪骗楚怀王的故事,为秦国强占了楚国的不少领土。一个组织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优秀的领导居中指挥,秦国能一扫六国成就统一大业,跟历任秦王都有巨大关系,他们的用人之道对秦国的影响更是举足轻重。 古人云:人才兴邦,得人才者得天下。三国时期,曹操提出“唯才是举”,哪怕“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的网罗,即使在当今社会里,有如此识见和气度的领导,也不多见。在曹操的影响下,曹魏*权名士刘劭撰写了《人物志》,这是一部专门研究人才问题的著作。全书共三卷十二篇,书中深刻讲述了识鉴人才之术、量能用人之方及对人性的剖析。刘劭在《人物志》里说:“夫人初难知,而士无众寡皆自以为知人”。由此感慨知人的困难,大多数人都自以为知人,反而忽略了人性的复杂。刘劭把才能分为三种:德、法、术。又将人才分为十二种: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每一种人才都有其相对应的才干和缺点,而一个人的才干又与其性格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所以事业就有大小之分,人才就有高下之别。 《人物志》指出,君主是用人者,使用人才的诀窍,是根据形势需要,安排适当的位置,协调彼此的关系。他指出:“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意思是说,大臣以能胜任某种工作为才能,而帝王却以能用人为才能;大臣以出谋划策、能言善辩为才能,而帝王以善于分辨和听取臣子的意见为才能;大臣以身体力行为才能,而帝王以赏罚得当为才能。因此,在讨论战略决策的问题,其实本质上都离不开人的问题。如果手下有着司马错、张仪这样的顶尖人才,那么考验领导者的是分辨和听取意见的能力;然而如果手下都是赵高、郭开这样的庸才,那么考验领导者的就是识人用人的能力。 然而,现实生活中,其实大部分领导者最欠缺的就是识人用人问题。《人物志》中讲,人在交往中容易“推己接物”,即以自己的观点和喜好对待他人和事物。事实上,绝大多数人都是优点和缺点辩证统一的,识人,既要识优点,更要看缺点,用人才能用其所长,避其所短。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责,就在于发现人之所长,使用人之所长,扬其长而避其短,趋其利而舍其弊。真正懂得用人的领导,眼里绝不会有无用之人,既然人才类型不同,能力大小各异,关键看能否准确为其定位,找到一个恰当的位置和恰当的发挥其作用的方式。如果一个领导者总是叫苦手下没有能干的人才,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刚愎自用,无法识人用人,导致真正的人才离他而去,最后留在身边的,只能是和自己一样的庸才。 自古,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ibue.com/bbzz/10764.html
- 上一篇文章: 读完一遍,相当于看了部历史纪录片,
- 下一篇文章: 部编版六年级下册第15课真理诞生于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