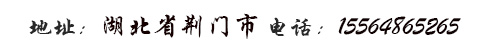王季思悲喜相乘中国古典悲喜剧的艺术
|
王季思(-),浙江永嘉人。戏曲史论家、文学史家,长期从事戏曲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著有《西厢五剧注》《桃花扇校注》等,主编《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全元戏曲》等。 中国的戏曲,是在东方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适应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背景和审美情趣。它和西方戏剧在具体表现上存在差异,毫不足怪。 西方的戏剧,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总结了古希腊时期广场演出的情况,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建立起悲、喜剧的审美观念,又指导着后来的戏剧创作和演出。中国的戏曲向来没有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也没有能够从美学上得到充分的认识和总结,因而在理论上仍是一个未经开发的宝库,有待于我们的积极发掘。 中国戏剧虽然没有像西方戏剧的源远流长,在理论上形成较为完整的体系,但戏剧的萌芽早在音乐的演奏和歌辞的创作中出现。这可以从《诗经·国风》中不少有人物故事,写人间哀乐的篇章和《楚辞·九歌》中写人神迷恋、徘侧芬芳的作品中得到印证。“悲莫悲兮生离别,乐莫乐兮新相知”(《九歌·少司命》),则综合了后世习惯用以概括戏剧故事情节的“悲欢离合”。它既包含了喜剧的因素,也包含了悲剧的因素。 《九歌·少司命》 随着音乐演奏和歌辞创作的发展,儒家的《乐记》为各种乐曲的不同性质及其历史背景作了分析。 这就是“治世之音安以乐”的“安乐”,“乱世之音怨以怒”的“怨乐”,“亡国之音哀以思”的“哀乐”。它对后来喜剧、悲剧的创作和评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下面试分四节谈谈个人一些初步体会。 一、从《西厢》《还*》的比较谈起 中国戏曲中的悲剧,不同于西方以剧中主要人物的死亡终场的悲剧;中国的喜剧,也不同于西方以滑稽、讽刺为主的喜剧。正如将唱、做、念、打融为一体而成为高度综合性的京剧一样,中国戏曲总是把喜怒哀乐的各种感情熔于一炉,而不是把它们截然分开,因而也给人以与西方悲、喜剧不同的审美感受。我们需要西方的悲、喜剧理论作为参照,但不能用西方的观念硬套中国戏曲,更要避免只在理论上兜圈子,而应当从具体作品出发,通过深入的理解、阐释,再提高到理论上来概述、来评价。这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态度。 我这里想就《西厢记》《牡丹亭》(《还*记》)的悲、喜剧的不同处理出发,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个剧本之为悲剧、喜剧,或悲喜剧,同它的结局关系最大。《西厢记》如果结束于长亭分手,就会是一部以生离结局的悲剧,《还*记》如果到“闹疡”结束,则将是一部以死别终场的悲剧。而死别的悲感,总是源于生离的。 《还*》的下半部如果到“硬拷”结束,柳生从被认作劫坟贼的罪犯一下子成为金榜题名的状元,它可喜的程度,显然也比张生从郑恒的造谣破坏中获得美满婚姻动人得多。 就《还*》全剧看,上半部是杜丽娘由生而死的悲剧,而下半部则不仅是杜丽娘由死而复生的喜剧,而且还以较多的篇幅演柳生由失意而得意、由逆境转顺境的喜剧。 合而观之,《还*记》既不是悲剧,也不是喜剧,而是传奇戏中较为典型的悲喜剧,即正剧,而《西厢记》则是比较典型的喜剧。 明人沈德符说“《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顾曲杂言》)在《西厢》流传三百年之后,《还*》给读者、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可想而知的。 《还*》虽是悲喜剧,但从艺术效果看,其悲剧处理更为动人。 历来的悲剧结局,如“秋夜梧桐雨”“孤雁汉宫秋”以及《西厢》的“长亭”、《拜月》的“走雨”等场子,俱以悲景衬悲情。这一手法可以溯源到宋玉的《九辨》:“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复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送将归”,以草木变衰的悲凉之气,衬托伤离怨别的悲情。 《牡丹亭还*记》 而《还*》的“惊梦”“寻梦”“闹疡”等场子,却把杜丽娘的满腔幽怨,放在姹紫嫣红的满园春色中抒发,把她的生离死别放在中秋佳节中演出,这真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它不是“以悲景衬悲情”,而是“以喜景衬悲情”。后来《红楼梦》写黛玉在宝玉结婚的乐曲声中“焚稿断痴情”,《杨门女将》在满堂喜色的祝寿场面中,忽传噩耗,杨宗保阵亡,寿堂变灵堂;都是以喜衬悲,用强烈的对比手法,收到意外的艺术效果。 前者如画家的“层层渲染”,是一层又一层加上去的加法,后者则如诗家的“反对”,起相反相成的作用,有点近乎乘法。“反对为上,正对为下”,刘勰的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还*》的“闹疡”曾使我想到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的《乡镇医生》,主要是两者中的女主人公都为爱情的渴望而死,引起我的联想。后者在艺术上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是写女主人公在爱情的绝望中,爱上了她缠绵枕席时偶然出现的医生,要求与他结婚,这死气沉沉的病房就改成了她临时婚礼的洞房。 郭启宏的《评剧皇后》,在评剧艺人白玉霜缠绵枕席时,宣布跟她的情人结婚,改病房为洞房,与此相似,都属于“以喜景衬悲情”,收到加倍悲痛的艺术效果。 正因为悲喜相乘可以产生更强烈的艺术效果,我们大可不必为中国戏曲中悲、喜剧的这种“不纯”而妄自菲薄。 二、悲、喜剧中情景关系的处理 悲、喜剧中情景关系的处理,可以分为四种: (一)以喜景衬喜情(二)以悲景衬悲情 上述两种出于常情常理,是抒情诗中常用的手法,在戏曲中也常见。 (三)以喜景衬悲情(四)以悲景衬喜情 后两种出于观众意料之外,又在人物情理之中,起到相反相乘的效果。这一手法,近乎事物发展中的突变、质变的性质。它能促使一个喜的故事突然转成悲,或悲的故事突然变成喜。运用得好,常常会带来意外的艺术效果。 元人杂剧中以悲衬喜的关目如《救风尘》《潇湘雨》等都是如此。《潇湘雨》的末折尤为动人,所谓“其境愈悲、其情愈苦”,后来转悲为喜、转苦为乐,情景乃更动人。西方喜剧,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磨刀霍霍,正待向安东尼割肉时,乔妆打扮的鲍细亚,以机智的辨才挫败了夏洛克,与《救风尘》《赚蒯通》的关目有可以相通之处。 《救风尘》 景物的悲或喜带有自然环境的特点。*河长江地处温带,春秋代序,四季分明,春天春光烂漫,给人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秋天秋风萧瑟,则容易引起悲怆凄凉之情。所以中国人对自然的这种感受比较敏感,而地处寒带或热带的人就不可能有这样的感受。人情的喜怒哀乐,是人类共通的。但中国人对哪些喜或不喜,这是由民族生活习惯形成的。如中国“四喜”,诗中的“久早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又以科举取仕的汉民族所特有的。 以喜景写喜情,《诗经》的《关雎》《桃夭》可以说是源头。以悲景写悲情,则《楚辞》的《九歌》《九辨》表现更明显的特色。我想这与前者流行于西周承平之世,后者产生于楚国衰亡之际相关。 因此,研究悲、喜剧,对于历史上悲剧性或喜剧性的文学作品也应注意。江淹《别赋》《恨赋》值得一读。《别赋》写生离,《恨赋》写死别,把中国人的悲哀情绪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别赋》)即是以喜景衬悲情,相反相乘,产生强烈动人的效果。至于《凤求凰》一曲对后世爱情喜剧的影响,《陌上桑》一曲对后世“发迹变泰”一类悲喜剧的影响,就更不必说了。 三、喜剧中的悲剧意蕴和悲剧中的喜剧情趣 在人类生活中,一帆风顺到成功,或一路倒霉到失败的事实都是少见的。反映到舞台上,绝少一直笑到底的喜剧,与一直哭到底的悲剧,而总是喜中有悲,悲中有喜的。前者可以说是带泪的喜剧,而后者则是含笑的悲剧。 喜剧引起人的笑,不应都是廉价的笑料,可贵的是一些含有深层意蕴的笑。打动人的方法也有不同的层次。有的人用的是台上故意出错、插科打诨、摆噱头的方式。这在悲、喜剧中都存在。而较深层的喜剧关目,往往是喜中有悲的。 《西厢》的“佳期”是崔张得到美满结合的喜剧关目。但中夜欢情正浓之时,莺莺却忽发悲音,向张生诉出“他日勿以白头见弃”的忧虑,就表现了封建时代妇女的可悲境地,而有着深沉的悲剧意蕴,比之泛写此刻的喜悦更加动人。“拷红”是红娘以机智、辩才挫败老夫人的喜剧关目,但红娘唱的一曲:“你绣纬里效绸缪,倒凤颠莺百事有。我在窗儿外几曾轻咳嗽,立苍苔将绣鞋儿冰透。今日个嫩皮肤倒将粗棍抽,姐姐呵,俺这通殷勤的着甚来由”?写尽了奴婢成为主子替罪羊的悲哀,同样表现了深沉的悲剧意蕴。这种悲剧意蕴,包涵有封建时代男女不平、主奴不平的深刻意义,加深了这些关目的思想价值。 悲剧中的喜剧情趣,大都通过净、丑的插科打诨来进行。《窦娥冤》中张驴儿去告状,县令桃杌反而向张驴儿下跪,说是“凡来告状的都是我的衣食父母”。《琵琶记》“义仓娠济”,一个借《上大人帖》打诨,自说家有三千七百口,被骂为“一口胡柴”,一个借《弥陀经》打诨,自说家有一千二百五十口,被骂为“佛口蛇心”,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但比之《桃花扇》的“投辕”、《长生殿》的“看袜”,显然后来者居上。“投辕”一场中,柳敬亭借口饿急,欲闯入左良玉内室,以激发左良玉,使他从“饿的急了,也不许进内”醒悟到引兵东下的错误。“看袜”一场,李摹看袜时想到的“绝代佳人绝代冤”,道姑则要把它当宝贝供奉,而郭从谨则破口大骂杨妃,使天宝皇帝弛了朝纲。这种带有喜剧性的场面,就都与剧本主题、中心人物或事件有密切关系,不是可有可无的闲文。 插科打诨,在悲、喜剧中都有运用。运用得好,可以活泼舞台气氛,引发观众会心的笑意。而悲中有喜的意蕴和手法,可以使观众的情绪得到调剂,但用得不好,就不免流于恶趣。这在汤显祖、洪昇等名家作品中都有所不免,应引以为诫。过去《西厢记》演出中,在张生与莺莺幽会之后,红娘见到张生,问他病情如何,张生道:病已好了九分,还有一分未愈,则在小妮子身上。这就非常庸俗,也有损于剧中主人公的形象。 《西厢记》插图 总之,中国戏曲中,喜剧里有悲的成分,悲剧中也有喜的因素,它不仅丰富了戏曲表现手法,也是适合观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情趣的。 四、中国古典悲剧与古典喜剧的美学感受 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决定了它们在悲、一喜剧表现上的差异,同时,也形成了悲、喜剧的美学感受的差异。 西方学者说悲剧给人以祟高的美。这对《精忠旗》的岳飞、《清忠谱》的周顺昌这样的悲剧人物是合适的;但对《汉宫秋》中的汉元帝、《梧桐雨》和《长生殿》中的唐明皇就不太合适,而对《琵琶记》中的蔡伯喈、《清风亭》中的张元秀就更其不合。 西方学者说喜剧给人以滑稽的美,这对《看钱奴》中的贾仁,《绿牡丹》中的柳五柳是合适的。但对《西厢记》中的崔莺莺、《拜月亭》中的王瑞兰就不合适。而对《救风尘》中的赵盼儿、《望江亭》中的谭记儿等喜剧人物更其不合。 这是因为我国戏曲传统与欧洲戏剧传统存在差异的缘故。西方戏剧起源于祭酒神的颂歌,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所以其悲剧强调严肃,追求通过“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观众的感情得到“净化”。因而悲剧中不允许夹杂喜剧的因素,而是在演完三出悲剧之后,再加演一出轻松滑稽的“羊人剧”以调剂观众情绪。这样,喜剧性因素便被排斥在悲剧之外,只作为一种附加的补偿物存在。古希腊悲剧主要表现高贵人物的悲剧,整个舞台气氛严肃静穆,给人以一种崇高的感受。而喜剧则向滑稽、讽刺一路发展,也不允许悲剧性因素掺入。两者严格区别,分途发展,而各达极致。其喜剧也以此之故,主要属于讽刺喜剧。西方的戏剧理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中国戏曲最初的萌芽虽然也与宗教祭祀有关,但秦汉以下渐渐转移到民间,所谓“街陌讴谣”,主要是娱人而非娱神,因而从一开始就按现实生活把悲剧和喜剧因素交互融入乐曲中,而不是把它们截然分开。所以悲中有喜,喜里含悲;既以悲衬喜,也以喜衬悲。其审美感受也较为复杂,不只是崇高和滑稽两类的判然分明,如果说西方戏剧将悲剧的崇高和喜剧的滑稽加以提纯而发展到极致,中国的戏曲则将两者揉合一起,互相调剂、衬托,不是强调怜悯与恐怖以达到净化目的,而是表现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中庸调节,达到明辩是非、惩恶扬善后的超越。这既是儒家积极入世的现实态度,又带有道家阴阳相激、刚柔相济的哲学意蕴,可以说是一种民族传统心理的积淀,也是中国戏曲通常缺乏西方悲剧震撼人心力量的原因所在。 明末清初的*周星在《制曲枝语》里有两句话说明他对中国悲剧和喜剧的不同感受:“喜则欲歌欲舞,悲则欲怨欲怒”。“欲歌欲舞”,显然不是引起满堂哄笑的讽刺性喜剧,而只能是歌颂性喜剧。它的美学感受,不是滑稽,而是优美。“欲怨欲怒”,表现两种不同类型的悲剧:哀怨剧和悲愤剧。哀怨剧如《琵琶记》《清风亭》,悲愤剧如《窦娥冤》《精忠旗》《清忠谱》。前者的艺术效果是缠绵徘侧的怨思,是从怨乐的传统来的。这一传统源远流长,传统诗歌中的闺怨诗、宫怨诗都属于这一类。其特征是儒家传统的怨而不怒,给人的感受是脉脉柔情,一片幽怨。后者的艺术感受则是怒发冲冠的壮气,给人以悲壮的美。从中国传统美学看,前者表现为阴柔之美,后者表现为阳刚之美。当悲喜相乘,阴阳两极碰撞时,就发出了眩目的火花。 阳刚和阴柔并不是截然割裂的,它们也可以达到相反相乘的效果。如《别姬》中,霸王表现的品格是阳刚的,但当他留恋虞姬、战马时,就带有阴柔的含蕴;虞姬主要体现为阴柔之美,但当她为鼓励霸王继续作战,慨然自刎时,则又有阳刚之气。两者结合,就给人以一种新的美感。它是难于用崇高或悲壮等词加以概括的。 总之,欧洲的戏剧理论,主要来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他们论崇高与滑稽,是符合西方戏剧的实际的,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如何吸收欧洲戏剧理论的成就,创造性地发掘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理论,仍有待于我们的积极努力。 (原注:这是我的博士生*仕忠根据我一次辅导课的讲授提纲和录音整理的。第四节里融入了他个人的一些见解。) 按:本文原载《戏曲艺术》年第1期。文中通过《西厢记》《牡丹亭》等剧作分析中国戏曲“以喜景衬悲情”的艺术手法。提出中国戏曲用悲喜转变带来意外体验的“悲喜相乘”理论。又比较中西方的戏剧起源与发展,提出“悲中有喜,喜里含悲”体现了中国儒家传统的中庸思想,是中国戏曲审美的基本特点。在相关研究领域引起广泛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baibue.com/bbzl/10551.html
- 上一篇文章: 新书推荐郑振铎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
- 下一篇文章: 白先勇昆曲无他,得一ldquo美r